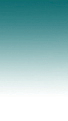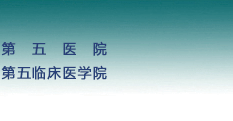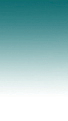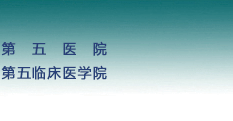2006年,我在加拿大Calgary大学血液病中心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一年.不单单在技术上学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一种对西方医学文化的心灵感触。
从医疗体制上而言,加拿大的高税制度很完善,高收入则高缴税,最多的可以达到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这些税收收入又比较公开透明地用在医疗和教育等公益事业上,所以加拿大的的医保、社保系统非常发达。即使对于低收入阶层,每年仅需要缴纳很少的医保费用就可以享受全面医保。患者入院时只需要把医保卡交给医院,医院的所有费用都经过医保中心付费,患者和医院之间没有任何费用的直接流通。这样对于病人和大夫护士而言,他们之间只是单纯的救治和被救治的医患关系,所以医患关系也就更加融洽。
我访问的那所医院相当于国内的三甲医院,但是病人却相对较少, 70-80%的疾病都在社区由家庭医生就诊治了。每个社区的居民都必须在家庭医生那儿注册,有小问题都先由家庭医生诊治,制度不允许病人直接去大型公立医院看病。除非急诊,一般患者即使去了大医院,医院也不予接待。对于大型公立医院而言,只接受家庭医生的预约。在加拿大,预约公立大型医院相关学科医生的权利不在病人,而在家庭医生。这和该国层次分明而完善的医疗网络密不可分。
不过,每项制度有利必然也有弊,加拿大的医疗体制一方面可以充分应用各方面的医疗资源,保证医生对于每个病人的接待时间和看病的质量,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延误病情的情况。家庭医生预约大型公立医院医生一般都需要大约四周左右时间,四周后,大夫的护士秘书会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家庭医生再通知病人。一般预约都是有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不过还好加拿大人都比较守时。比如血液科病人,如果大型公立医院大夫看完后需要做骨髓穿刺,那么就再预约,说不定会约到十天后,骨髓穿刺结果出来后再预约医生对结果进行判断,如此这般他们看病的时间周期会非常长。尽管我们常说国内“看病难,看病贵”,但和国外严格的预约制度相比,国内无论什麽级别的医院也无论什麽级别的医生,患者只要挂上号就可以当天看上病,你说国内看病真的还算“难”吗?相反,许多中国人在国外得了病都会回国来看,尤其是恶性疾病,就是怕延误了病情。
值得国内借鉴的还有西方国家的死亡教育。与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心理不太相同之处在于,许多西方人在心里都对死亡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可能缘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可能缘于他们从小受到的关于如何面对死亡的教育。在国内的话,肿瘤诊断一般都会对患者本人隐瞒,而在国外,患者病情告知制度要求不管病人得了什么病,必须告诉本人,而包括妻子或者父母在内的任何亲属如果想知道患者的病情,未经患者同意都不能告知,否则就是违法。作为一个个人,有权利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有权利选择治疗的方案或者面对死亡的方式。这点也避免了国内存在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求知道病情唯独患者本人被蒙在鼓里,患者本人的生命和健康却由别人定夺的现象,同时避免了在关键时刻非医疗因素引起医疗纠纷的隐患。
另一方面,加拿大对医生的人文化教育贯穿始终,常常有一些和病人面对面交流的课堂。比如血友病是一种慢性疾病,讲课时,老师会将病人和他的家人请到课堂,与医学生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从如何知道这个孩子得了血友病,家人面临过怎样的艰难,又如何互相扶持积极应对,他们以一个家庭为单元一点一滴款款讲述。医学生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某一种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病人身后活生生的家庭,以及一个个有病人的家庭里酸甜苦辣的真实故事。在这种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医生的悲悯之心很自然培养了起来。
从血液病的技术层面而言,无论诊断标准,治疗方案,我觉得加拿大和国内相差不大。但是,他们比我们规范很多,标准化很高,所以每个病例资源的可分享度很高。另外,他们的优势更多的是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更注重致力于研究清楚疾病的发病机制,发病的可能环节,耐药机制等,每个临床出现的细小问题都可能成为他们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科研严谨程度还是值得我们努力学习的。 总而言之,医疗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之所以和西方国家有差距,问题来自于方方面面,虚心借鉴,合理采纳,我想咱们国家的医疗也会逐渐好起来。 |